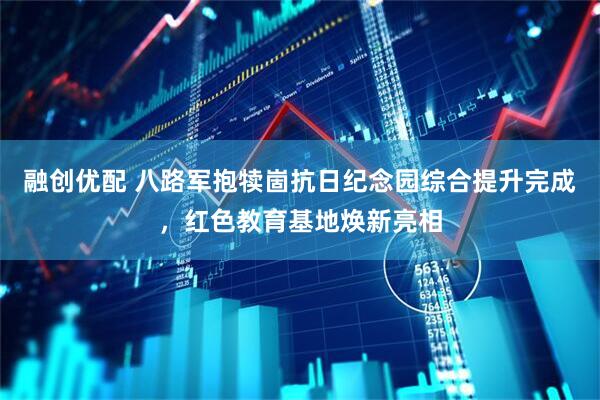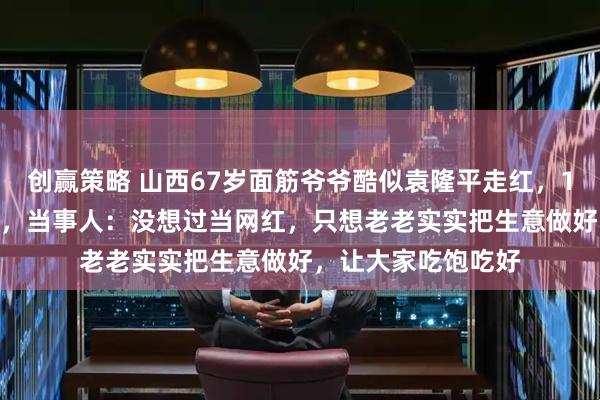百事达配资 米芾:风樯阵马云山照

家乡的米公祠,是年少的我常去之处,总是莫名的亲近百事达配资,似乎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奇士,并未一刻离去。初记事时,我就对这位米公充满好奇。
米芾一生,恰似北宋江河上的一叶风樯,于墨海砚山中劈波斩浪。他笔下的草书如阵前战马,锋芒所向处,金石为之开。
米颠拜石,文人风骨独一格
无为,又名“濡须”,一川碧水蜿蜒过青灰色的城墙,岸边的垂柳蘸着墨色,将千年光阴揉碎在涟漪。
我站在无为米公祠的墨池畔,恍惚间似见一位宽袍大袖的文人掷砚惊蛙,素宣翻飞处墨痕化作游龙,在北宋的天空写下"无为而治"的注脚。米芾与这座江淮小城的缘分,恰似他痴恋的太湖石,嶙峋中藏着通透,癫狂里透着赤诚。
崇宁三年的秋阳斜斜铺在无为军衙门的青砖上,新到任的知军米元章还未卸下行囊,便被庭院中一尊太湖石摄了魂魄。此石"高八尺,周身两人合抱不及,状貌奇伟,多孔多窍,似胖人形",他整肃衣冠,执笏而拜,口称"石兄",从此晨昏定省如待至亲。
衙役们窃窃私语,笑这大人怕是得了疯病,却不知这"米颠拜石"的痴态里,藏着士大夫对天地造化的敬畏——石不能言最可人,嶙峋风骨恰似他"与物无竞,与民无扰"的为政之道。也许艺术追求的极致需要精神上的“洁癖”。这位出身勋戚世家的贵公子,本该在汴京书画舫中谈玄论道,却因耿介性情被放逐到"月十日无一递,无一过客"的僻陋之地。他在《与友人书》中自嘲"坐井底尔",却将满腹才情倾注于斯。
展开剩余87%春耕时节率官员扶犁亲耕,夏日催农人抢收抢种,秋日登稻孙楼观再生稻穗,冬日凿墨池建投砚亭。百姓只见他袍袖沾泥,却不知这位俯身田畴的知军,正以笔为犁在江淮大地上书写"善察民怨"的政绩,让无为小城化作"鱼肥稻香"的乐土。
宝晋余韵,臻于极致米知军
无为米公祠原名宝晋斋,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无城镇西北隅,是米芾任无为知军时于崇宁三年(1104年)所建。在他去世后,人们于米公军邸的旧址上建米公祠以示纪念。
米芾崇尚晋人书法,在获得王羲之《王略帖》、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、王献之《十二月帖》墨迹后,视为珍宝,自题斋名“宝晋斋”,以收藏晋人书画作品。 原斋毁于兵火,明万历二年和清乾隆元年两次重修;乾隆三十七年,县守张公侨摹陈洪绶所画拜石图刻于碑;三十九年县守张琨玉始建拜石轩、书画舫和香月亭。清咸丰元年又毁于兵火,光绪丁丑年知县王峻再次重修。
如今漫步修葺一新的米公祠,宝晋斋的晋唐碑帖在粉墙上投下斑驳光影,聚山阁的飞檐挽住流云。 宝晋斋中,晋人法帖的墨香与灵璧磬石的清响交织。米芾在此将王献之《中秋帖》临至乱真百事达配资,却自嘲"集古字"终成自家面目。他的"刷字"绝技,源自对褚遂良"熟驭阵马"笔法的顿悟,更融汇三峡江声的韵律——"三峡江声流笔底,六朝帆影落樽前"(《望海楼》)。墨池深处,仿佛可见他"一日不书,便觉思涩"的执着,也仿佛可见其书法用笔迅疾劲健、欹纵变幻、痛快淋漓之势。苏轼论其书法:“风樯阵马,沉着痛快”。黄庭坚更说:“如快剑斫阵,强弩射千里”。
这位"米颠"的精神洁癖,在艺术领域臻于极致,在生活中留下趣闻。
某日周仁熟唾沫试砚,他当即赠出心爱之物,因"砚石已污,不可复御"。这般近乎偏执的纯粹,恰似其《水调歌头》中"涤尽荒凉境,散作尊前喜"的追求,要在混沌尘世辟出方寸清明。就连择婿亦要名"段拂字去尘",将生活琐事皆化作美学仪式。
江声裂岸,元是知音难再觅
元祐四年秋夜,米芾在涟水(今江苏涟水县)海岱楼观潮,见月光倾泻如银,万道虹光孕蚌珠,提笔写下"天上若无修月户,桂枝撑损向西轮"(《中秋登楼望月》),此间气魄,正是"风樯阵马"的具象——既有桅帆破浪的孤勇,又有战马踏云的凌厉。
这位自称"楚国芈氏后人"的狂士,常以奇崛姿态示人。 这般佯狂背后,藏着文人的傲骨:宁向无知顽石折腰,不与浊世同流。正如李东阳所言:"平生两膝不着地,石业受之无愧色"(《怀麓堂集》),这般"癫",实乃对精神世界的坚守。
米芾之“颠”遇到东坡之豁达,成就另一番动人景致。
元丰五年的黄州江畔,贬谪中的苏轼与青年米芾初见。酒酣之际,东坡命其将观音纸贴于壁上,挥毫作枯树怪石相赠。米芾后来自述:“始专学晋人,其书大进”。这场相逢,如同晋人风骨穿越时空的接引——苏轼是渡船人,米芾是寻碑客,他们在笔墨江河中完成了宋人对魏晋的朝圣。
白发东坡抚米芾背叹:“今则青出于蓝矣。”彼时米芾已创“刷字”绝技,却仍以北面弟子礼相待。米芾的书法以“刷字”自称,他写字运笔迅疾而劲健,笔势跌宕起伏,整体气势磅礴,独具一格,后世书影响深远。二人最后一次在金山(今属江苏镇江)对饮,苏轼病体支离仍笑谈:“待不来,窃恐真州人俱道,放着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,不别而去也。”
月余后东坡病逝,米芾闻讯作挽诗:“招魂听我楚人歌,人命由天天奈何?”(《苏东坡挽诗五首 其五》)墨迹未干处,尽是知音绝响的苍凉。后世甚至有人托米芾之名写下“先生去后行人断,一树梅花寂寞高”的句子,更增加“伯牙绝弦”之意。
墨池星斗,且以天真写性灵
某个蛙声如沸的夏夜,水心亭里的烛火明明灭灭。米芾正临摹王羲之的《王略帖》,忽闻池中群蛙聒噪百事达配资,竟提笔在砚上写个"止"字,扬手掷入荷塘。神奇的是"蛙声顿寂",池水渐染墨色,成就了"墨池"传奇。
这则载入《无为州志》的轶闻,倒像是他艺术人生的隐喻——以癫狂破拘束,用天真写性灵。
三百年后,清代诗人颜尧揆任无为知州,在《初晴步墨池》中感慨:"绿柳四围眠复起,欣然人在水中央"。这"欣然"二字,恰是米芾留给无为的精神印记——在宦海沉浮中保持赤子之心,于礼法拘束里守住文人本色。 清代另外一位诗人吴克俊漫步墨池畔,写下"过眼云烟剩墨痕,墨池人去一楼存"(《稻孙楼怀古》)的怅惘。
这“楼”便是“稻孙楼”。 据记载,米芾出知无为军时,建造了西门稻孙楼,并为其书额。秋日西门城楼竣工时,米芾登楼远眺,见水稻割后复穗,老农告知此为“稻孙”,米芾大喜,遂题西楼为“稻孙楼”。无为城在历史上历经多次战乱与自然灾害,城墙和城楼多次受损又修复。1939年,国民党县长率众拆城,6门城楼全部拆除,周围城墙拆矮半截。“稻孙楼”佳话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近于湮灭。
幸而今墨池犹在,垂柳依旧轻抚明代重立的"墨池"碑,池畔投砚亭的石桌仿佛还留着未干的墨渍。馆中珍藏的157方碑刻中,最令人驻足的当属《章吉老墓表》,字迹如"游走飞动"的龙蛇,记载着章吉老这位无为名医、针灸圣手的仁心仁术,也凝固着米芾对民间疾苦的关切——笔锋起落间,既有士大夫的担当,又有艺术家的悲悯。
天人交感,至今空羡米家颠
他一生痴迷奇石,据《宋稗类钞》记载,米芾听闻安徽灵璧石奇特,便向上司请求到距灵璧石较近的涟水做官,以便获得灵璧石。 米芾得灵璧石“研山”后,如获至宝,连续三天抱着石头入睡,后挥毫泼墨写下《研山铭》,以表达对研山的喜爱之情,此作也是他艺术创作巅峰状态的体现。这件神品与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《兰亭集序》并提,被称为“天下第一难书”。
这奇瑰的成就,源自他二十余年对艺术朝圣:从濡须河畔拜石,到灵璧山中采磬,再至海岱楼头望月。正如其词云:"宝月圆满时,夜光值千金"(《蝶恋花·海岱楼玩月作》),他将自然之魂熔铸笔端,使笔墨成为天人交感的精神图式。
他在《宝晋英光集》自述:"功名皆一戏,未觉负生平",宦海沉浮终究不及与石兄对酌、同云山私语来得真切。
晚年的米芾愈发亲近禅宗。建中靖国年间,他于汴京大相国寺观怀素《自叙帖》,忽有所悟,挥毫写下:“一扫二王恶札,照耀皇宋万古。”这般狂语惊动朝野,却暗合禅宗“呵佛骂祖”的真谛——唯有打破桎梏,方能见性成佛。
大观元年深秋,米芾预感大限将至。 他将苏轼所赠紫金砚交予长子:"传世之物,岂可与清净圆明同去住"。 他焚尽平生珍藏,自备楠木棺椁,食宿其中七日。临终前召集亲友,诵偈云:“众香国中来,众香国中去。人欲识去来,去来事如许。”言毕合掌而逝。
这般谢幕,与其说是死亡,不如说是将肉身化作了最后一幅书法——起笔癫狂,收锋圆融,留白处尽是生命的禅意。这位被徽宗笑称"书画船"主人的奇士,最终化作润州丹徒山麓的一抔净土,而他的精神早已融入文明长河——今日米公祠内,百方碑刻犹自诉说"风樯阵马"的传奇。
我伫立在无为洗砚亭前,仍能看见那个对着顽石高歌的身影:"宇宙如浮梗,醉卧不知醒"(《水调歌头·中秋》),这是对功利世界的疏离,更是对永恒之美的朝圣。 米芾以癫狂为盾,守护着文化命脉。他像《苕溪渔隐丛话》描绘的"雪蓬烟艇",虽无三湘七泽之壮,却独得"风樯阵马之奇"。
明朝何景明题诗《米元章拜石图》曰:“节比岩岩志比坚,冠裳下拜也堪怜。此意世人谁解识,至今空羡米家颠。”是为知音乎?
苕溪留影,米氏云山今何在
苕溪位于中国浙江省北部,流经余杭、德清等地,水系分为东、西苕溪两大支流,两溪在湖州市北白雀塘桥交汇后注入太湖。 米芾常乘舟载书画游览江湖,也包括 苕溪 。黄庭坚曾作诗“万里风帆水著天,麝煤鼠尾过年年。沧江尽夜虹贯月,定是米家书画船”(《戏赠米元章二首 其一》)来称赞。
米芾元祐三年(1088年)从无锡去往苕溪时创作行书《苕溪诗帖》,真迹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与《蜀素帖》并称米书“双璧”,是米芾行书风格成熟的代表作品之一,对元代赵孟頫“复古”书风、明代徐渭大写意行草均有深远启发。此帖曾藏入南宋绍兴内府,历经明杨士奇、陆水村、项元汴、梁清标等藏家,后入清乾隆内府,并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
今日立于苕溪畔,犹见当年“米家书画船”的倒影。水波荡漾间,仿佛听见米芾吟哦:“满船书画与明月,十日随花窈窕中。”这轮照耀过北宋的月亮,依然在洗墨池中圆满,在云山图里朦胧,提醒着后世:真正的艺术,从不是规矩的囚徒,而是用生命写就的,最狂放又最温柔的诗行。
米芾之子米友仁,承袭了父亲的血脉与癫狂。
他幼时见父挥毫,常以手指蘸墨在墙上涂抹,米芾非但不斥,反笑言:“此子得我墨中三昧。”小米十二岁作《楚山清晓图》,烟云吞吐间已有“米点皴”雏形。成年后,他于《潇湘奇观图》中独创“落茄点”,以水墨横点写江南雨雾,世人谓之“善画无根树,能描朦胧云”。黄庭坚观其画作,曾叹:“元晖(米友仁字)笔底有江南湿润气,较乃父更得造化之妙。”
这对父子的艺术对话,常现于笔墨交锋。某日米芾见子作《云山图》,提笔在空白处戏题:“老米画山如画佛,小米画山如画雾。”米友仁当即续写:“佛在雾中观自在,雾随佛影入空无。”这般禅机对答,恰似他们的“米氏云山”——父亲以骨法立山势,儿子以气韵染空灵,合为水墨乾坤的双璧。
米氏父子的故事,恰似他们笔下的水墨云山,老米以奇石为骨,筑起文人精神的险峰;小米以烟雨为韵,晕染艺术传承的长河。从无为米公祠的拜石遗韵,到故宫《苕溪诗帖》的飞白苍劲,他们的癫狂与坚守,早已超越书画技法,成为中华文化基因中的一段风骨。
夜色中的濡须河静静流淌,两岸渔火映照着新编的无为鱼灯舞。这座城市将"米芾书画研究会"的笔墨融入长三角文脉,用板鸭的醇香延续"物阜时和"的期许,恰似欧阳修笔下"无为道士三尺琴,中有万古无穷音"(《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 其一》)的余响。(作者:左格拉)
发布于:福建省科元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